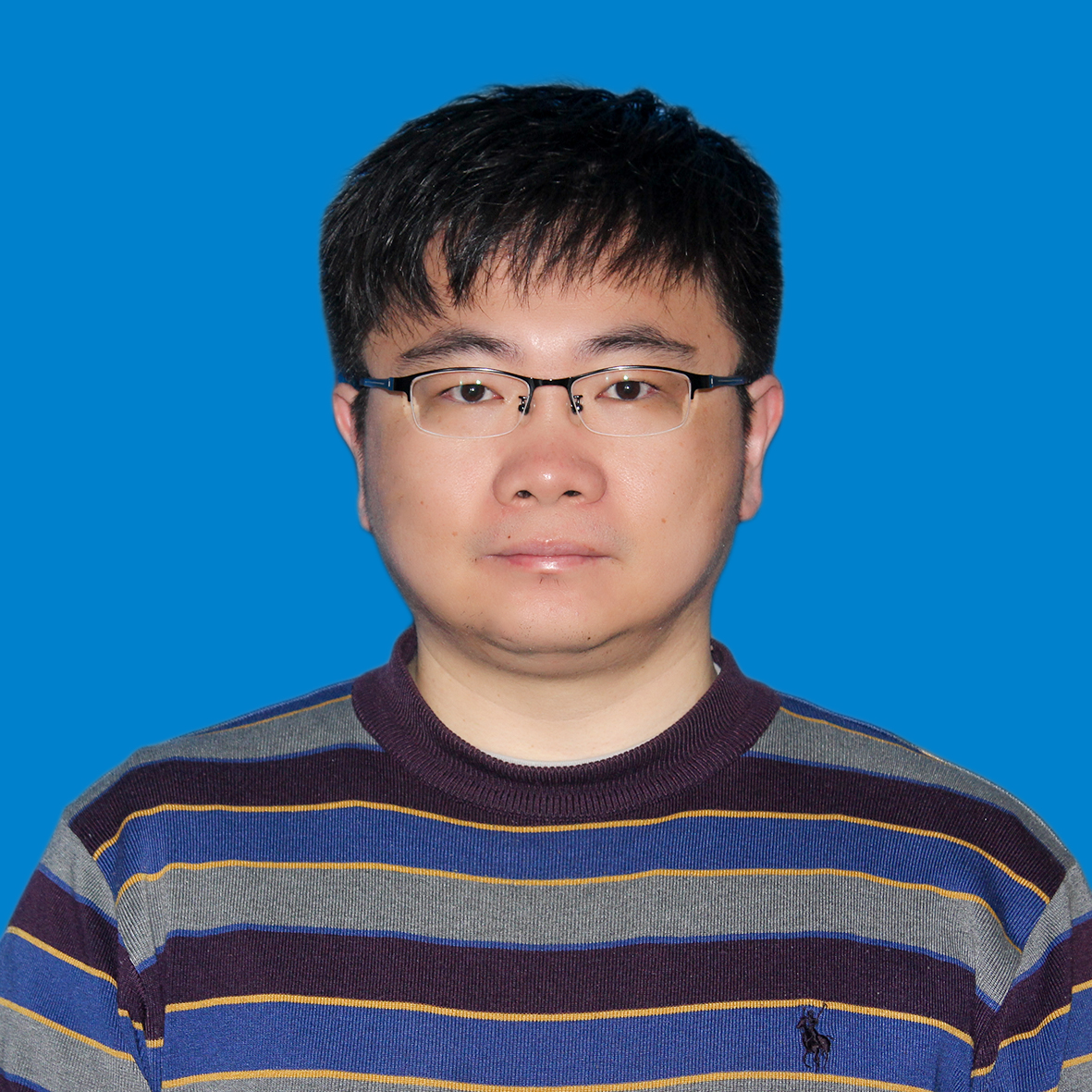俞允强老师二三事
此文是我大三时所作,文笔稚嫩。2003年12月12日发表于北大未名BBS天文版。文中可以看到我初学宇宙学时的激动、感悟,暗藏着我最终选择宇宙学为事业的草蛇灰线。感谢时任版务(也许是李然,不确)的合集,20多年后居然还能找回。2022年12月21日,俞教授因感染新冠,遽尔作古。特重录此文以示怀念。文中所有的物理学概念错误及错别字,除改正了梁灿彬老师的名字和一处离谱的错误以外,一仍其旧,以存原貌。其时年少张狂,文风轻佻,乃时代原因,在所难免,读者谅之。
皮石,2022年12月22日
前几天上完了俞老师的本学期的最后一节课,听说明年他就不再教广义相对论了,别的可不知道还教不教。前年的时候就听说他要退休而且“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返聘”(见他关于电动力学课程和本科生教育所写的短文)${}^1$,心里惶惶然。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得他还是并没有退休。02、03这两年他上半学期开广义相对论,下半学期开物理宇宙学。
很早就想写点关于俞老师的东西。我也不是牛人,听俞老师的课往往一知半解且经常几个问题问得他连连摇头。在他眼中即使有关于我的记忆,也绝对不会认为我是个好学生。但是在我的心中,俞老师永远是最优秀的。这次他当选十佳教师,名至实归,但是关于俞老师的介绍总是《电动力学简明教程》《广义相对论引论》《热大爆炸宇宙学》那几本俞老师著作封二上的“作者简介”${}^2$,似乎过于呆板。故顺便在此写点关于俞老师的小东西,希望抛砖引玉,能得到一同聆听俞老师教诲的诸位同学的共鸣,借此向俞老师表达我的敬意!
(一) 第一次接触是在大一上学期的时候,那时对物理学和天文学一窍不通同时也不知道这些学科的研究方向。但是就在那时候看见三角地贴了一个通知说,物理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俞允强老师要做讲座,题目是“大爆炸宇宙学”。当时一看就觉得很有意思。小时候看过卞德培老师写的《宇宙奇观》,里面讲过宇宙膨胀、大爆炸等很当时听起来很玄乎的东西,我当然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讲座在物理楼三楼进行,我去的时候叫上了老张${}^3$(导致现在的一个结果就是我经常和他辩论,我不是他,但我大致也能猜测这次讲座对他的影响同样巨大)。我们到达的时候里面已经坐了半教室的人,前几排清一色的都是白头发老头,排场不小。过了一会,在一个年轻人的引导下(就好像11月24号晚上讲座时的陈弦${}^4$),同样白头发的俞老师慢慢走了进来。那时候他还没有现在这么老(感觉这两年他老得厉害),头发并不是完全白的,还有很多黑的呢。走路的时候腰也没有现在这么弯。 那天与老师讲座的时候用的是幻灯片,但是我仍然想办法把内容基本上都抄下来了。真是太精彩了,那时候我的激动心情怎么形容也不为过。是俞老师在我们面前打开了一扇窗口,打开了一个世界。讲座内容基本上和他的物理宇宙学的课的是一样的,但是被严格浓缩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又能讲得那么富有吸引力,这和有的老师讲课的时候经常讲不明白完全是相反的。俞老师可谓是抓住了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学的精髓,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这门物理学前沿课程通俗地介绍给大家。在那次讲座上我得以一窥广义相对论、相对论天体物理、宇宙学之妙,直至现在那种物理学美的余韵仍然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讲座结束之后,俞老师让我们提问。于是我提了一个,关于宇宙学的基础问题。俞老师说宇宙学只需要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学原理就可以推导出很多有效的结论。我问道,我们的宇宙学中为什么没有热力学呢?为何不在宇宙学中运用熵的概念和方法呢?当时我们还没有学热学,我对热学是一窍不通,但是这一窍不通却问了一个现在看来都很棘手的问题。 俞老师的回答却很冷淡。他说(原话我已经忘记,现在是根据自己的记忆重新构筑的),我们考虑的宇宙学是动力学意义上的,对热力学二定律并不涉及${}^5$。然后他就去转而回答一个女孩子提的“宇宙学中为什么没有黑洞”的更弱的问题了。 现在看来老俞的冷淡自有其道理。因为在宇宙学的意义上分析熵本来就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远一点可以扯到克劳修斯的热寂,近一点也有彭罗斯的两种奇点的分类。老俞显然不愿意在这件事上面扯太多,更何况是对一个看上去像个高中生的小孩。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牢牢记住了俞允强这个名字。在我看来,惠勒、索恩、霍金、彭罗斯们离得太远,实在是难以捉摸。而俞老师在这里,就成了爱因斯坦思想的火炬在北大的唯一代表。
(二) 第二个学期我就选了俞老师的“热大爆炸宇宙学”。上课第一天俞老师说,虽然这个可是通选课,但是非常难,希望只是想了解一下概念的同学不要学这个课,或者说不参加考试,欢迎来听。我本来也想是不是不要考试了,后来一想,他讲课深入浅出,焉有听不懂之理! 听课内容和他后来出版的《热大爆炸宇宙学讲义${}^6$》差不多,但是看书绝对也没有上课听他讲讲得清楚。两年之后的很多课程内容在我脑子里都已经不剩下什么了(我本来就不是好学生),但是这宇宙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却在我脑海里盘旋,后来竟使得我在学习任何科目时,都习惯性地看看它在宇宙学中有没有对应内容,能不能在宇宙学中运用,等等。 这学期俞老师开的课是“广义相对论”,照例拉了老张去听,一次又一次的在周三的下午感受实实在在的物理学大餐,简直是无与伦比的享受!从仿射空间到黎曼几何,从场方程到黑洞,每一步都是那么美妙而简单。 俞老师上课的特点是物理思维占主导地位的。如果你看他的书,就能发现很多数学在表达方法上不尽“严格”,推倒上过于简单。可是这种方式恰恰是从繁杂的数学中迅速理出物理要领的关键。上课时也是一样,如果推导过于复杂,他就会说“我们不进入细节”(这句话在宇宙学课里面经常说,但是在广义相对论里面说的不是很多了);如果你这时候去查查书,就会发现书上是一大堆令人望而生畏的复杂的计算。我个人以为俞老师的这句话是最能体现他风格的地方,就是抛开复杂的数学推导,直接从复杂的数学公式中得到问题的物理本质。而这正是和很多年轻教师们不同的,也是和其他很多教相对论的老师们不一样的。热统的老师${}^7$曾经调侃自己说,我成了高数老师了。电动老师${}^8$也经常把一节物理课上成复变函数。我也曾经听过几节北师大梁灿彬老师的广义相对论,复杂的数学弄得我晕头转向。但是在俞老师的课上你始终能够把握住问题的物理精髓。俞老师经常告诉我们的是物理的本质,那是最重要的。 我的毛病就是往往在数学中把物理迷失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很不能接受《广义相对论引论》中的不严密的数学。我甚至认为Riemann几何=广义相对论。我认为数学应该建立在完整的Riemann几何的基础之上才行,像俞老师那样的讲法,无乃大简乎?俞老师对Riemann几何一笔带过,却花了大力气去讲观测量的理论,而这些在我看到的Riemann几何的教材里面都没有涉及。结果是一个月之后我对物理学的看法彻底改变了。物理学并不是加在数学上的彻彻底底的附庸科学,而是很独立的。数学只是语言。
(三) 老俞讲课有很多小细节很有意思。当时上课地点在一教。他每次上课都来得很准时,绝不会早到。到了之后一般先到楼下买一瓶统一冰红茶,讲课间隙就会喝(可能是距离办公室太远,自己带水不方便吧?这次在物理楼讲课的时候他喝得水就是自己泡的茶,茶叶很粗,不是特别好,而且一般泡得很浓)。上课时间一到,底下的学生们还在喧哗着讨论,他就会莞尔一笑,说道:“我们——开始(读平舌)吧。”上课每当讲到一个段落时他就会总结一句“那么好了”,然后就开始讲结论。 昨天下午讲完本学期最后一节课之后,学生照例鼓掌。俞老师向台下微笑,表示感谢。就好像一个艺术家,他的作品得到了人们的欣赏。夕阳透过物理大楼的窗子上照在他略显佝偻的身体上,却在身后堆满了方程式的黑板上洒下一个高大的背影。这是我在北大见过的最美丽的景色。
注解
-
这篇文章原题为《一封公开的汇报信——致北大领导》,大约在2002年2月发表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主页上的“物理论坛”栏目。2017年左右,此文以《北大物理系俞允强老师的公开信》为题在微信公众号上再次流行。全文可在袁岚峰老师的知乎页面查看。点击此处。
-
这段作者简介如下:俞允强,1937年出生。195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2年在意大利的SISSA获天体物理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教授,理论物理博士生导师。他长期讲授各种理论物理基础课,一直颇获好评。近十余年研究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学,也讲授相关课程。他的研究论文和教学工作都曾多次获奖。
-
张振辉,现任河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讲师。
-
陈弦,2001级天文系学生,班长。现任北京大学天文系长聘副教授,副系主任。
-
现在看来,俞老师的意思是,讲座只涉及宇宙学的动力学部分即均匀宇宙的演化,不涉及到早期宇宙的粒子物理和核物理过程。
-
俞老师在宇宙学方面一共出过三本书。1995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爆炸宇宙学》,是中国的第一部宇宙学教材。此书只印了1000册,现在很难找到了。经过修订之后,2001年改为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热大爆炸宇宙学》,我选该课程时还不知道这本书,当时手抄的讲义有两大本。此处指的就是这本书。2002年,俞老师根据多年来授课的讲义出版了《物理宇宙学讲义》。
-
当时的“热力学统计物理”授课教师为马中水。
-
当时的“电动力学”授课教师为郑汉青。